愈发传统的老家
母亲抱怨现在睡眠不好,父亲开始批判:“你就是不会快乐,一天到晚絮叨。人快乐了,细胞就有能量了。”
母亲放到厕所的糕面发霉了,父亲又批判:“你摸到面是干的就是干的吗?敞口放着能发霉吗?我看你就是认知有问题,怎么能那么自以为是?”
我看「出走的决心」那部电影里,姜武没我父亲演的好。
就这么件小事两人又吵了半个多小时,或者说是父亲单方面的指责和母亲的辩解。
这样的对话听得我愈发头痛,但搞不好他们乐在其中。不如带上降噪耳机做我自己的事情。
更有意思的是,伴随着父亲对母亲的洗脑,或者母亲对自己行为的合理化,母亲也认为一个有本事的女人就是可以把家料理得井井有条。然而几天之后的我,意识到母亲的处境要痛苦得多。
本来今年过年不打算要压岁钱的,但老家的风俗讲究,没结婚的都是小孩。结了婚就是大人,要给小辈压岁钱。不存在不给也不要的可能性。琢磨了一下反正压岁钱也是互换,不如把收到的压岁钱留给爸妈好了。
姥姥和姥爷看着非常老了,我收了压岁钱打算拿给父母。母亲想让我单独给姥姥姥爷钱,我直截了当地拒绝了。这是他们的父母,赡养父母是他们的义务。就算按照法律上来说,我都没有继承遗产的权利,自然也就没有赡养的义务。就算从儒家传统上讲,我越过父母给姥姥姥爷钱,那也是他们的不孝。
山西看似变得更加传统,但这种传统甚至更为变形和落后。更像是洋不洋土不土的一种扭曲规则的集合体,一方面要求父母对子女婚姻和育儿无休止的付出,另一方面又要求子女对父母付出一切不能远行紧密团结在父母周围。而只要有一方不守武德,那这盘子就得玩崩,变成一方对另一方的残酷剥削。
和父母一起去某个远房爷爷那里拜年。从父亲拿些不太好的年货过去,又把用过的纸巾随便放在单元门口的行为来看,他对这家人是有些想法的。想必是因为年轻时,这房亲戚极其有钱,却不愿意借钱给非常贫困急需买第一套房的父母。但现在父亲发展的好了,就开始每年频繁上门。
听说爷爷的女儿还没有找到对象,父亲便自告奋勇的介绍自己单位的年轻人。我有幸见到了一次父母间快速的信息勾兑,他身高如何,老家是哪里的,父母是干啥的,工作能力怎么样。老家体制内的人,相亲了一轮又一轮,都是那一些资源。
父母晚上又在拌嘴,我发现自己已经很难忍受这种吵闹,宁愿一个人躲在房间带上降噪耳机来求个清净。
姐姐的女儿刚六个月大,我在她家找到了一本儿歌书,专门有一节来讲传统文化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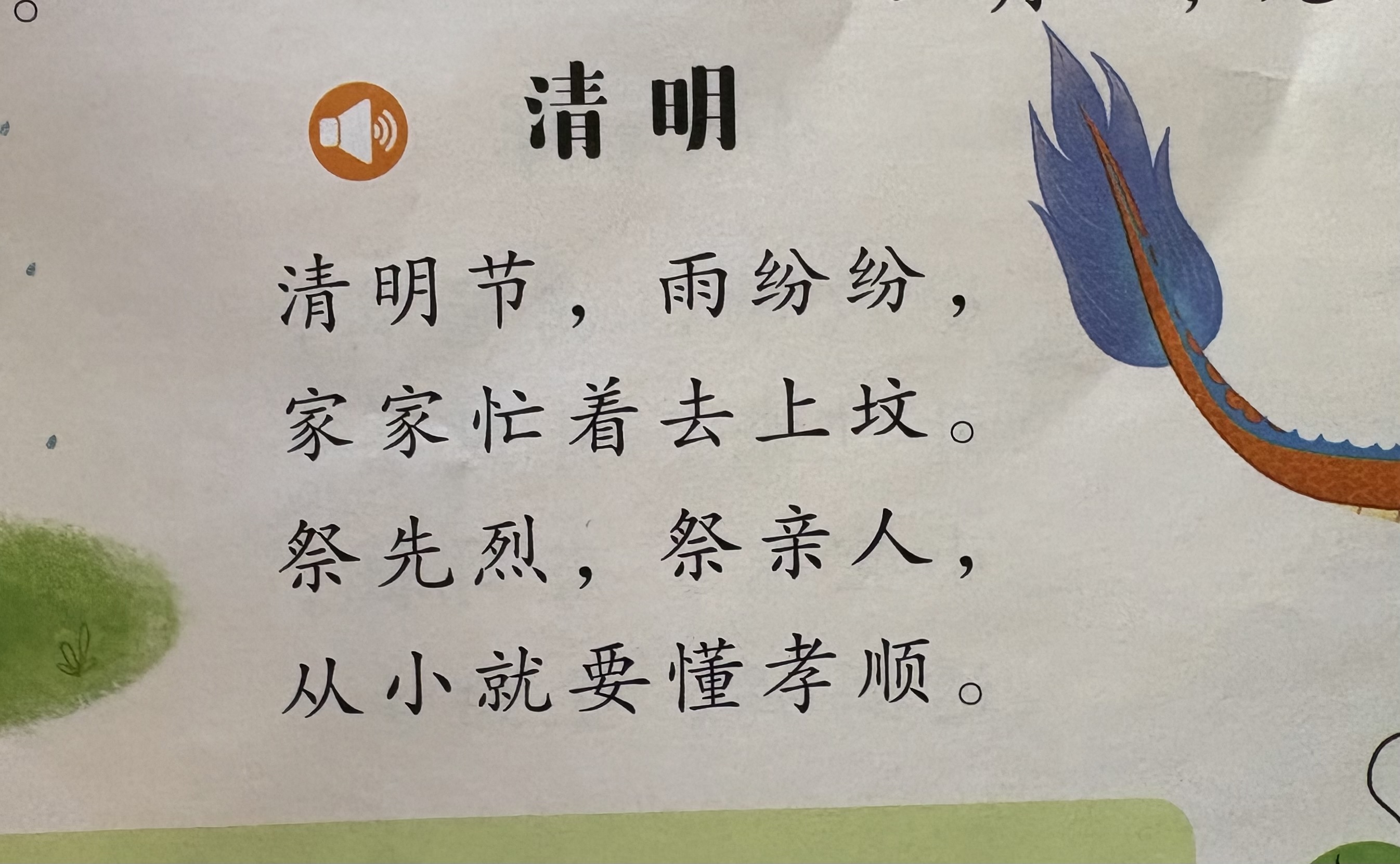
意识形态的教育要从小抓起,真是优良的传统。这让我想起了小时候一段时间国学热,我爸妈搞了很多塑料卡片让我背国学经典,其中主要是「弟子规」。
即使在正经的国学中,弟子规也是纯粹的垃圾,假托圣人语言的洗脑之物,更不用说国学本身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了。可悲的是,这些强行塞到我大脑中的垃圾,至今我都能脱口而出。
这让我又在反思,看来我对父母开明的看法让我忽略掉了很多童年时期的迹象。实际上他们从一开始就是站在传统一方,所谓的开明只是没时间管我的表现。
吃年夜饭的时候,得知姐夫的母亲来自有钱人家。她的爷爷在公私合营时,留人不留财,活了九十八岁。怪不得他们对吃非常讲究,会自己卤肉,也会买品质非常好的菜。
虽然两家人的钱差不了多少,但我姐夫从小就有任天堂的游戏机来玩。只有不被匮乏折磨过的人,他们的后代才能真正拥有生活。受过苦的人,他的下一代就需要奋力从这种苦难造成的精神疾病中挣扎出来,而只有第三代,才能真正活的自由。很不幸,我就是那个需要挣扎的第二代。
姐夫的父亲很喜欢他的孙女,用各种方法逗她开心。六个多月的孙女也一定要缠着他,人类幼崽小小的就能分辨出爱。
家里用的是马桶,我上完厕所习惯把马桶垫放下来。母亲说要掀上去,不然男人要往垫子上尿。我说他自己都要坐下来上厕所的地方,还往上尿?有女人在家里马桶垫要放下来,那是方便得坐着上厕所的女性,而且最好男女都坐着上。
从上厕所就能看到男女的权利差别,根植于每一点细节中。
回家的路上,聊起清明祭祖的事。母亲突然问我知道我们家的祖坟在哪里吗?活了二十多年从来不知道啥是祖坟,这几年却突然又开始祭祖搞活动。看来当年的几场运动还是没能彻底拔除掉地方宗族文化,党还是不够给力。
回了老家,女人们在灶台做饭洗碗,男人们抽着烟,琢磨着怎么给家族的下一辈们谋个好营生。稍微有点志气的,如我的小表弟,连过年都不想回来,借口饭店过年也要加班。
但他要是回来了,每年挨长辈训了,那就能换个稳定而体面的工作。这地方如同黑洞,掉进来的人再也出不去了。
如我这般去了遥远的大城市定居的人,也就彻底离开了家族,成为了无根之人,不必祭祖,不必露面,也不必参与家乡财产与资源的分配。乡土逻辑从来不讲法律,只讲共识。大家认为是你的,那才是你的,与法律无关。
听到父亲可能要把奶奶接到成都来耍,又听说他和母亲要直接过来,根本没问过我是否愿意,有没有时间。这就是拿了别人的代价,这个空间似乎根本没有拒绝别人进入的权利。这彻底熄灭了我继续投入时间和资源,装点空间的想法。无恒产,便不必有恒心。手伸太长的人,根本不知道收敛。
当然,这一切似乎可以终结于结婚。结了婚就不用领压岁钱,就在大人那桌吃饭,能加入家庭会议。但这实际上都是幻觉或者陷阱,结了婚后就从家族资源的受益者变为了需要扶持家族的人。过去家族的所有投资都要看得到回报,而家族控制的触手甚至可以延伸到伴侣身上。
没看到吗?围绕着锅台转的,那都不是本家的女人。所以他们为什么要催婚呢,因为看不到回报的漫长投资,不会有多少耐心残留。
我姐结婚后,居然给了我五百压岁钱。我们可是同一天出生的,就因为结婚与否似乎分成了两辈。
这一套乡土逻辑实在是令人厌恶。
那么如何打击我这种将在外,君命有所不受的想法呢?深谙党内政治斗争手段的父亲,想必也会想出不少非常犀利的方式。比如回家的路上问我会不会给他钱,比如教训其他子辈时对我含沙射影,比如不时的侵犯我的空间来彰显主权。
但正如红色权力压根管不住资本市场的大溃逃,只要自己关键的生产资料不被控制,那不还是想怎么活就怎么活。所以最核心的路线始终都应当是扩大自己的收入来源,增强自己的生存能力, 最好还能手头有对抗或制衡的筹码。
通过观察父亲处理很多事情的操作,可以看出独权专断、睚眦必报和猜疑嫌忌的性格特点。曾有一次,因为某个人没给他做的事帮忙给两百元钱,就不再帮他办事。而另一位愿意给钱的人,很快就帮忙解决了低保。他甚至会处心积虑隐蔽意图,从细节中长期观察某个人的性格,并借此做出自己的判断,进行打压或提拔。他很看重别人对他的帮助是否感恩,是否毕恭毕敬得顺从。
老家也有微妙的权力结构,收入最低最没地位的小叔开会坐一边的小凳子上,甚至开到一半就出来和我的母亲一起来洗碗。
我的母亲为何要去洗碗呢,剩下的两个婶婶为何不用洗?
在家族内部的权力分化中,父亲夺得了高位,那是否就需要母亲来洗碗以示对他人的安抚?母亲在回来的车上说,谁也不洗碗,又不忍心让手上很多伤口的奶奶来洗,那就只能自己洗了。
母亲似乎比之前更加看重家庭关系了,变得更加敏感,似乎总觉得自己给别人做的还不够多,总觉得娘家似乎收到了不公正的对待。包括和小姨聊天,都瞪着眼让我和他们多说几句,丝毫不管我和他们没什么共同语言。后来我才明白,母亲想通过对兄弟姐妹好来换得一些社会支持。
母亲停不下来看短剧,姐姐的手机里充满了短剧和轻小说,父亲捧着手机看着传统秧歌。虽然都有体面而稳定的工作,但精神都似乎非常空白。
今年我不要压岁钱,父亲在那里说:「嘿,小钱不要,大钱不是还得要么」。今天还问我将来舍不舍得给他们花钱,这实际上就是匮乏的后遗症,这让我觉得给父母钱都有点恶心。我突然对花钱毫无心理负担,花就花了,怎么样。
在之后的交流中,聊到了上一次我想出去玩时,为什么父亲最终不再折腾。他透露了最关键的想法:「那是因为你用自己的钱出去玩,但凡你用我的钱,我就把钱抽回来,就算扔到水沟里也不给你」。当我开始自己工作挣钱后,实际上已经脱离了控制。而且就连他放在我这里的钱,甚至也没有任何可能要回来,他还能打官司起诉我不成?前脚打官司,后脚进监狱。
临走前两天的晚上,父母又为了给姐姐女儿多少压岁钱吵了起来。母亲坚持要给一千,说别人都是这么给的。父亲开始爆炸:「这次给一千,以后是不是要给几千。钱都是你这么花没的,你就闭嘴吧。」我都能感到母亲的绝望,东亚家庭始终无法学会好好沟通。但在匮乏和恐怖之下长大的人,又能表现出多好的品行呢?
对维舟老师的一句话非常有感觉,越了解中国人,越感觉到绝望。我想这种绝望其实含着某种慈悲,不是本性坏,实在是日子太苦了。
随着他们争吵的升级,互相开始狂丢伤人的话。父亲说出了那句非常经典的话:「你自己一个月能挣多少,出去你能活下去吗?不怕以后账分开算你又能怎么样」。然后开始历数去年母亲生病花了多少钱。钱和资源就是他用来控制人的最后手段,所以他对于吃拿毫无心理负担,尊敬与厌弃张口就来的舅妈一点办法都没有。
我察觉到父亲想一劳永逸解决麻烦,而母亲似乎也要彻底崩溃。我便开始客串心理咨询师,分析当前的处境。我认为母亲是抑郁了,她现在无力、焦虑和攻击性都是来自于心理上的痛苦。母亲认为苦难都是父亲造成的,想来我的城市。但这不是解决的办法,我连自己都还没能摆脱父权的恐怖。
最终我以自己为例讲出了一个叙事,母亲抑郁了。她的攻击性来自于想要自救的念头。想要走出抑郁,可以靠舍弃被疾病影响的扭曲的自我,通过全身心的对别人好来获得力量,最终拯救自己。而在父权制下,这个别人只能是父亲。因为亲戚只会仇恨我们落井下石,朋友又不可信任。
母亲该怎么做?我总结出了几条原则:「父亲永远是对的;听他的话,感他的恩,跟着他走;心中浮现的任何抗拒的念头都因为自己生了病」。行动上就是听父亲的话,不与他争辩,遇事让他拿主意,好好做饭收拾房子对他好。然后通过一心一意伺候父亲,来获得真正自我的喘息空间。
最有趣的是,这些话我是当着父亲的面说的,他连连点头不断肯定,「服务好我就是最大的事」。直到最后品出一点味来才补充一两句「我也很理解人,你妈就是不会开心,开心了啥事没有。」
我没有说出来的话是:「获取他的信任,掌握他的钱财,等他一退休失去政治资源,拿着钱直接消失」。这是最彻底的反叛,也是最狠辣的绝杀,比现在争取一点所谓的平等和关爱要现实的多。父亲以为他可以稳稳拿捏母亲,但母亲若是来这么一手,他又能怎么办?
现在我的父亲就已经把所有的钱交给了母亲掌管,但从不让她花钱。这个状况被父亲渲染为「我把一切都给了你」,从而获得对母亲精神控制必要的负罪感。某种程度上说,父亲也试图对我用这一招。虽然这一招对善良的母亲很有用,但对于觉醒后的我,几乎是瞌睡给我送上了枕头。这其实是母亲和我最大的优势,钱在我们手上,于是命也在我们手上。
实际上,父亲把钱交在我手上是危险的。对于精通权力斗争的父亲,自然也是知道这一点的。当爷爷想把自己手头的几十万分给几个儿子,来换取日后的孝顺时,我父亲直接阻止了他,并把钱自己保管了起来。他知道把钱发给孩子,只会迅速被花完,要的时候一分都不会剩下。所以父亲把钱放一部分在我手上唯一的目的,就是规避某种调查。然而,对于我把钱花掉的恐惧一直折磨着他,这当然就是我用来斗争的筹码。
说回到父母的关系,父亲至今不愿承认母亲抑郁了,甚至认为只要强制开心了就不抑郁了。母亲因为抑郁不能劳作时,又只会不断的批判。父亲没救了,但母亲还能自救。
实际上,母亲的抑郁应该去找优秀的心理医生,但首先每小时数百上千的花费必然是掏不起的,小城市也没有像样的心理医生。离开这个父权的有毒环境,跟在我身边也许可以改善,但这实际上也与我形成了不健康的共生关系,最终害了彼此。靠她逃离并自救,这对于一个病人的要求也太高了。
母亲在自己的手机备忘录里,除了父亲和其他家人,还给自己建了一个文档,名叫“自己加油”。记录了自己身体上的病症,还有抑郁情绪。父亲看到了这个文档,说:“干嘛这么关注负能量,要有正能量。”我看到只有心疼,母亲想自救,可身边毫无能帮助她的人。
中国底层女性的悲哀就来自于此,救济渠道的匮乏,有毒的父权压迫,没有高质量的社会支持系统。能怎么办呢?
父亲想要母亲变成什么样子呢?当母仪天下(家族)的皇后,一心一意侍奉的嫔妃,温柔似水崇拜有加的爱人。他虽然说着自己的一切都是为了母亲,但实际上只是拯救让当年结婚时被瞧不起的自己。他一生最大的信念就是成为那个小山村里最厉害的女婿,成为家族中权力最大的话事人。他经常挂在嘴边上的就是:「你要造反了不成?我狠起来自己都吓人,再惹火过去扇你两巴掌」。家中的一切都是他挣来的,大事小事都应当去请示他。他就是领导,话说出来就得执行,就算有不同的意见那也先执行了再汇报请示。
父亲的书架上摆着很多毛泽东的传记,对毛读过十七遍资治通鉴津津乐道。同样是学历不行,同样善于玩弄权术,毛是他的精神导师。
家族里的其他人呢?当然是对此恨之入骨,他能成事,也能让别人一夕倾覆。亲戚们不会感激他,甚至会逮住所有的机会试图摧毁他,但却又不得不服从他谄媚他。每个人的心中都充满着被压迫的恨意,父亲知道,但他自信自己掌握了所有人的命脉,自然毫不畏惧。我最优秀的一个表妹,研究生即将毕业,父亲迫不及待地展示自己的资源,告诉她应该怎么规划人生。我最聪明的一个表弟,为了躲开跪服的命运,一个人独自在外地打工,却受限于糟糕的经济环境,最终不得不向父亲求一份差事并许诺回到家乡。父亲可以肆无忌惮地当着兄弟的面,批判他兄弟的儿子是个废物,然后自己给他安排一份工作来享受这种拯救的感觉。谁能忍受?谁又能说什么?
父亲对姐姐的控制可以说是登峰造极,姐姐买的房子都在同一单元的楼下。令人窒息的距离,但却被父亲当作最好的决策洋洋自得。姐姐的每一个人生决策都由父亲做主,甚至去了大学都得每周回姑姑家。
对于我,父亲自然也是想施加控制。当然那些拙劣的手段对现在的我毫无用处,但时时刻刻处于警惕和对抗之中也让我疲惫不堪。还是那句话,只要我生活的根基未被掌控,他又能耐我何?
母亲不懂权力运行的机制,亲戚在她耳边表达对父亲的恨意时,她本能地感觉到自己需要做些什么,也许是对亲戚更好一些?也许是控制一下父亲的行为?所以父亲也说:「我现在感觉你在联合外人反对我。」
权威不可撼动,所有人必须服从。
这一套熟悉吗?
极权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皇帝能够决定的,这是深入到社会骨髓血液,下沉到哪怕亲密关系的两个人之中的毒素。爱情或亲情是最小单位的政治,一个人的政治观点从来都不可能和处理亲密关系的方式分开。极权传统毒害了我们所有人,还美名其曰优秀的传统文化。
这番叙事的影响力如何?经过一天的实践,父母之间的争吵少了很多,母亲也睡了久违的一个好觉。本来不打算再给钱的父亲,又拿了一些钱给我,认为我彻底长大了。父亲还开始在家族群里发一些治家的传统智慧,似乎自认了皇帝的位置。他们喝下了这些迷魂汤,并将其当成可以拯救生活的良药。
有代价吗?当然。母亲对父亲的顺从,会在灵魂深处带来别的痛苦,逐渐找回的自我会质疑这一切的意义。从彻底的顺从中重新找到反抗的可能不容易,但至少保留了反抗的火种。最终的出路,只有彻底的离开。
临走之时,我看到了姐姐的痛苦。她生孩子时因为孩子过大,做了会阴侧切,恢复了非常久。虽然现在带孩子不用出力,有保姆和婆婆,但这都是有代价的。代价是再生一个,直到生出男孩。姐夫一家人都有这个要求,父亲也认可,但只有母亲和我对此嗤之以鼻。现在姐姐和姐夫不再避孕了,这份苦难也将继续下去。
我姐姐惯于沉默,我也没能找到单独的机会与她聊天。我只能从母亲那里知道她不想再生了,但就连话都不能说的老家,又能有多少自由呢?
回家短短几天,见到了老家彻底的贫瘠和荒芜。所有人如同孤岛,或是深海中挣扎的溺水之人。庆幸我能离开,也需要更加努力来让自己走得更远。
Chat: [email protected]